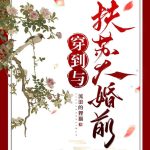整個地下建築內的區域劃分全部是用屏風來設置的,每兩個區域之間都有六到八張屏風相隔,把所有的七個區域劃分的倒也齊齊整整。
隔在金銀和青銅鼎之間的是六張超級大的三十頁紫檀木屏風,兩米左右的高度,寬度應該在十二米往上,每一扇全部都是花鳥紋的镂空雕刻,看起來應該是在整板上搞出來的。這麽大的尺寸,又都是上好的紫檀木,工藝也十分的到家,這可是名副其實的大手筆啊!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年代稍微有些短,都是鬼子六那個時候做的,可即便是這樣,也都很了不得了。
一般來說,高檔的屏風都是用紫檀木來做整板或者外框,這樣镂空雕刻的,只要搞錯一處,那這一張板子就算是廢了。想要做好,就必須得具備不計代價和有足夠的高級匠人,首先這四十多公分的紫檀整板就很難搞,在那個年代裏,也只有皇家貴胄能夠做到了。
而且從尺寸上來說,四五米的屏風就算是大號的了,一般的都在兩米左右,達到八米以上就要算是巨型的,十米以上的已經算是極為罕見,這十二米的超大紫檀木镂空老屏風,反正張辰是沒有見過。
金銀和文玩之間的隔斷,也一樣是紫檀木的镂空雕刻屏風,不過要比另一邊的六張要小一些,紋飾也不大一樣,是十張二十頁的山水紋屏風。但山水紋想要用镂空的手法表現出來就更加有難度了,雖然只有八米多的尺寸,但是勝在工藝更好一些。
時不我待,整個地下建築裏的東西數量難以計算,張辰和寧琳琅也顧不上仔細欣賞這些古之大匠的傑作了,反正回去以後有的是時間,現在最重要的是收納。
把這十六章屏風收起來,又看了一眼靠裏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鼎,張辰還是決定先去看看靠外一點的文玩,在所有的古玩文物之中,張辰對于青銅器的喜好并不是最大的。
自小就是在張百川的教育下,對書畫類和古籍類的東西吸收了很多的知識,再有董老和李天平的指點,在玉器和瓷器等方面也有不少的知識積累,這兩年以來,所涉獵的範圍也越來越廣。
卻是唯獨對青銅這一項,從小就沒有作為最重點的來學,只是出于不得不學,不得不通曉的無奈。而且自從用意念力淬煉過之後,大腦的發達程度暴增,在學習的同時把青銅的知識也都吸收了,所以才顯得在青銅方面同樣比較突出。
之所以選擇去看文玩這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哪一排排的多寶閣之中,有一只上邊擺放着的全部都是銅香爐,而且其中的兩只還甚是與衆不同。
張辰也是見過大世面的,別說小小的香爐了,禹王九鼎那樣的物件也都在他的手裏,二十幾只香爐基本是難入他法眼的。但是這一架上的香爐确實不同,雖然他手裏的東西有數以萬計是比這些東西還要高的,可奈何這樣的東西他手裏沒有,所以也就自然而然地物以稀為貴了。
如今張辰手裏的藏品上百萬,卻沒有一只正經的宣德爐,這也着實是一個遺憾。而宣德爐偏偏又是很多藏家都比較向往并且夢寐以求的寶貝,能夠有一只宣德爐,說出去那可是很有面子的。
當初在例行的鬥寶大會上,任志不就是想要用一只宣德爐來奪魁的嗎,當那只宣德爐出現的時候,任志的表現就已經是那種奪魁後才會有的了,可見宣德爐的魅力之大。可惜的是他那是一只假爐子,不但沒給他帶來想要的地位,反而把馬上風也搭上了,最後還被馬上風敲了不少的錢財了事。
宣德爐得名于大明宣德三年鑄的風磨銅香爐,後世模仿者數不勝數,也留下了不少的仿制精品,但是存世的卻是少之又少了,而宣德三年的更是屈指可數。
現在市面上的宣德爐也可以說能用數之不盡來形容,當然其中絕大部分是現代的仿品,毫無價值可言,充其量也就是個百八十的成本而已。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晚清民國時候的,甚至撞大運的話也能找到晚明或者清早期和清中期的,那價值就要更高一些,最好的也有很不錯的價值,但是相比于真正的宣德三年貨,品質就要差很多了。
就張辰送給老爺子張問海用的那只,就是清中期仿品之中比較精致的,當時花了很少的錢搞到手,也算是撿了一個小漏,到現在估計也能值個三二十萬的。
當時任志拿出那只贗品爐子來,還真把張辰給懵了一下,那爐子的确是很漂亮,做的也很仿真,如果不用意念力去觀察的話,很難在第一時間就發現問題。最開始的一剎那間,張辰甚至都有些羨慕馬上風了,搞到那麽漂亮的一只爐子。
現今存世的名爐張辰也見了個七七八八了,真正符合宣德三年品質的不過雙手之數,其他很多都是在宣德朝之後制作的,也有幾只滿清時候的仿品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
當然不是說那時候的人都在仿制宣德爐盈利,那時候的宣德爐雖然也有很大的名氣,卻遠遠達不到今天的程度,再說那時候的人作假還沒有猖獗道現今的地步,基本都是以樂趣和欣賞為主的。
尤其是一些皇帝下令仿制的,就更加沒必要以盈利為目的了,一個皇帝弄這個,他能賣給誰呢。再折回來說,如果真是以盈利為目的的,那就更要做到精益求精了。老年間能有空惦記宣德爐的人,除了乾隆那樣自以為天下第一,把玉琮當辋頭的傻X之外,可真沒幾個好糊弄的。
張辰才多大啊,離三十還差好遠呢,哪怕是有意念力幫忙,也有很多缺憾是自身彌補不了的。寧爺在收藏上搞了大幾十年了,民國的時候就饬查古玩界,那時候的玩意兒可比現在多多了;尤其是到了歐洲之後,走了多少的國家去憋寶,硬是沒拿下一只正品宣德爐。
整個張辰的師門裏,這麽大的一個群體,包括陳老、董老、張百川、李天平等等,也是沒有宣德爐在手的。據說當年張辰的師祖手裏有過一只,但是卻在清末戰亂的時候給丢了,自此以後師門中就再沒出現過宣德三年貨。
可見真正的宣德三年貨是多麽的稀少,現如今一只都已經到了幾百萬甚至更高的價格了,依然是有價無市,手裏有貨的都是不怎麽在乎錢的,誰舍得放出來呢。
不止張辰興奮,寧琳琅也是看着眼直,前面不遠處的多寶閣上,可是擺放着二十多只香爐,從外形上看基本都能和宣德爐挂上。鬼子六在當時可是排名第一的王爺,手裏的好東西絕不會少了,這麽多裏邊有個一只兩只的,也不算什麽稀罕事吧!
剛剛都把心思放在清點金銀的事情上,現在弄好了,注意力自然就投入到其他的事務上。兩個人快步走過去,一邊走,一邊使勁地頂着那些爐子,就怕是一眼不看爐子就能跑了似的。
張辰在過去的路上,已經釋放出意念力去觀察了,成色果然不錯,最少的也有三層綠色的光芒,最多的九只表面的綠色光芒達到了九層,這裏邊很可能就有宣德三年的啊!
兩處之間相隔并不遠,幾步之間已經到了那只多寶閣前面。
寧琳琅拿起一只差不多二十厘米的直徑,七八厘米高度,表面略呈淡金色的雙耳爐子,在手裏細細地摸了一遍,上邊的些許灰塵全部褪去,在強光燈的照射下反射出刺眼的光線。
用手稍微把燈光遮起來一些,裏裏外外地仔細看過之後,把爐子舉在張辰面前,想一個小孩子一樣,興奮道:“師兄你看,這真的是宣德爐诶!看看這表面,實在是難以言喻的細膩,我看着應該就是宣德年間的了,你來看看,到底我看的準不準啊!”
張辰早已經用意念力觀察過了,這只的确就是宣德三年的宣德爐,貨真價實如假包換,但是在爐子的一個足旁邊有益處小小的磕傷,品相已經不是這裏邊最好的了。
不過也不能打擊寧琳琅的高興,笑着接過寧琳琅手裏的爐子,看了看才道:“嗯,我的小師妹真棒,眼力一流啊,一出手就是真正的宣德三年貨。這爐子的手感細膩是判斷宣德爐的一個關鍵,真正的宣德三年貨使用的料子是經過十二煉的,在不停的鍛打中,把料子裏的雜質全部弄出去,剩下的就是精華材質了。又經過幾百年的使用和把玩,表面的包漿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厚實且混潤,已經呈現出佛經紙的色澤,的确是宣德爐中的上上之品。來,給師兄親一個,以資鼓勵。”
寧琳琅給張辰在臉上親了一口,嬌斥一聲,給了張辰一個結實的白眼:“師兄,你又來了,真是色心不死。真沒想到啊,居然是這麽大的一座寶藏,我感覺我們還會有更大的收獲,我們還是先把這裏的事情弄好了再做其他吧!”
說完又拿起另外的一只爐子,這只爐子和普通的有些不同,是一個長方形開口的。大約二十公分的高度,二十公分多的長,十二公分左右的寬,兩端是豎立的朝天耳。
寧琳琅看了看有些拿不太準,問張辰:“師兄,這只爐子從某些特征看起來應該也是宣德三年的,但是這種包漿和顏色卻不在五色之內,又是一只方形四足鼎的樣子,我實在是有些拿不準,你來看看。”
張辰微笑着接過爐子,這只正是讓他很感興趣的兩只之一。這只爐子的确是和其他的不大一樣。首先它的器型就與衆不同,有些類似于方鼎的形狀,鼎足和鼎身的高度都快差不多了,這種樣式的宣德爐別說是在宣德三年,哪怕是在整個宣德一朝的遺物,以及後世的仿品當中,都是沒有見過的。
雖然沒人見識過,但沒見過不等于沒有。如果放在一個普通的收藏愛好者手裏,這只爐子九成九是要抓瞎;哪怕是一些已經入行了的,或者入行有些年代的人,也不一定能夠頂着巨大的壓力,把這只爐子收下或者是堅持為這只沒有歷史記錄的爐子辯護。
真正能夠做到這些的人,也只有很少數的一些老爺子,和那些一心撲在文物研究上,知識儲備達到了一定的量之後的人,抱着琢磨和研究的心态,一點一點地去推敲分辨,最後給它驗明正身。
寧琳琅年齡雖小,可他從小就跟在頂級高手的身邊,她的父親弗雷德裏克,也是古玩方面的一把好手。來到京城後,又有一大票的高手給她指點,天天和張辰這個妖孽混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種凡是遇到拿不準的東西就去推敲和琢磨的習慣。而不是從潛意識就開始拒絕上當,一旦有了疑似仿品的嫌疑就會向看着燒紅了的炭塊,恨不得離得遠遠的。
而她的這種習慣和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張辰對她的影響,包括盧俊義、石磊他們,都潛移默化地有了這方面的傾向,并且在撿漏協會中大範圍的擴散。這種現象的出現,源頭就是在張辰百發百中上,而張辰本人總是從每一件玩意兒的細處抓真相,來證明他的眼光完全無誤。
寧琳琅把爐子遞給張辰,就是要張辰來告訴她,這只爐子是不是宣德三年的。如果真是,那應該從哪些方面來證明;如果不是,那又是什麽年代的,又應該怎樣判斷。
幾乎每一個跟張辰在一起淘過東西的同齡人和朋友師兄弟都會有這樣的認識,但凡拿不準的就去找張辰,只要找到他手裏,那就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寧琳琅和張辰在一起的時間最長,兩人之間的這種合作也是最多,張辰自然是知道她的意思。
接過香爐在手,張辰先是拿起香爐看了看款識,完全符合宣德爐款識的兩大标準,不過這個事屬于少數一類的那種,比常見的多了一橫。
接着再把意念力釋放出來,穿透表面上流行着的九層綠色光芒,進入到爐子的實體之內,自喜地觀察着爐子內部的分子構造,以及一些不同密度的金屬熔合在一起後的變化規律。
這只爐子張辰剛才在遠處的時候就已經盯上了,首要的原因就是它與衆不同的外形,卻又在年代上比較有說服力,如果真能證明這是一只宣德三年的爐子,那豈不就是蠍子拉屎獨一份了嗎?
可這樣的玩意兒不像書畫、瓷器等作品,有很多成形知識可以借鑒,整只爐子上面只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款識,再無其他明顯的辨識目标。若是一般的藏家,這個時候想要辨識真僞,恐怕就只能是依靠科學的碳十四半衰期鑒定了。
類似這樣的情況張辰之前也遇到過,處理的方法也很簡單。一是通過意念力的作用來放大物體的每一處,來尋找可作為理論的細微線索;二是将意念力穿透進物體內部,從內部的分子結構來判斷物體本身的材質。從而得出一個合理的依據和正确的判斷。
正經的宣德爐都是在宣德三年出來的,使用的基本材質是從暹羅國進貢的風磨銅,另外還加入了其他的一些金、銀等等的貴金屬,以致爐子的質地已經特別的細膩,再經過十二次的鍛打,材質就更加的精純了,這個特點是其他爐子所不具備的。
雖然後來也有人通過同樣的手法,使用同一批工匠制作過,但在整個制作的過程和工藝方面,還是有這樣那樣的缺陷,難以達到真正宣德爐那樣的效果。
張辰在收藏這一行當中,在意念力上受益頗多不假,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得益于他的專研和細心,否則不可能達到現在的效果。
就在宣德爐這一道上來說,張辰所依靠的可不只是意念力的神奇,為了能夠尋找出更多的辨識方法,他所作出的努力要比一般的收藏家多處很多。
宣德爐的基本材質是風磨銅,張辰曾經專門從泰國買來少量的銅礦石,在實驗中心用古老的風磨方法提煉出金屬銅,分成若幹份之後再加入不同的其他可能出現在宣德爐中的貴金屬,親自上火進行十二次的鍛打。
制作出了一批仿宣德爐後,通過肉眼和意念力,以及一些現代的科技手段,從各方面綜合檢驗這些爐子和材質,這才得出了先進最為科學和可靠的标準。甚至張辰還親自把幾批不同材質的料子進行了十五次鍛打,并且做出成器,然後和十二煉的材質進行對比。這裏邊所下的功夫和辛苦,遠遠不是一般的藏家所能比得了的,同樣他所得出的數據和知識,也遠超出一般藏家的見識範圍。
也正是因為這樣,張辰才能看明白這只不同尋常的宣德爐,也只有他才能真正明白這只爐子的與衆不同源自何處,這即是所謂的“付出總有回報”。
通過不斷的努力和學習,張辰現在可以說已經是鑒定宣德爐的天下第一高手了,寧琳琅之所以首先到這只多寶閣上看看,不止是因為她知道張辰對好爐子的渴望,而她也很願意在家裏或者唐韻增加宣德爐這至關重要的一項,更是因為她對張辰鑒定宣德爐的能力。
事情就是這麽的巧,之前張辰在實驗中心的時候,因為突發奇想,曾經把燒制青花瓷的钴料加入到一塊爐料的廢料中,打出了一只很小的爐子。那塊料子又因為在鍛打的初期就加入了金、銀和錫等金屬,再結合钴的放射性作用,出來的爐子在淡金色中又有些微藍色,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爐子,顏色雖然比較怪異,倒也顯得甚是獨特,別有一番味道。
張辰沒想到的是,他并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早在五百多年前的明朝,就已經有工匠嘗試過這樣的爐料組合配方了。而且很顯然,手裏的這只爐子在爐料配合的比例上,要比他當時随意添加的玩鬧之舉正規很多,考慮到了錫的藍色和钴料化學反應後的藍色之間的調和,以及钴的放射性對于金、銀、銅等金屬的影響,呈色淡金帶微藍,完全是一件成熟的藝術品。
所以在剛剛看到這只爐子的時候,張辰的心髒很不争氣地狂跳不止,能夠找到一件五百多年前就用類似方法制作的爐子,雖然作者已經逝去很久了,但是就這麽一點點相同之處,卻是牢牢地把兩人的思想凝結在了一起,這也算是萬裏遇知音了吧!
通過意念力對爐子內部構造的了解,內部的分子排列和不同金屬相熔合後的結構和正品的宣德三年爐相比,除去有錫和钴的成分,以及放射效果之外,都是完全相同的。張辰已經很确定,這的确是一只宣德朝禦用工匠親手制作的爐子,而且所用的爐料也确定是宣德三年那種十二煉的料子。
最為關鍵的一點,也是這只爐子最與衆不同的一點,就是因為在料子裏邊加入了一定比例的錫成分,使得這只爐子歷經五百多年,在不同的環境中被把玩和放置,還在這不見天日的地下建築中存放了一百多年,卻能夠保持完全沒有氧化和生鏽,這一點是在其他爐子上不曾有過的。而這爐子內腔中的香灰,和煙熏後所造成的痕跡,也能夠找到宣德三朝的證據,只是這爐子是否皇家使用的貢品還不能确定,也許只是工匠私下裏偷偷弄來玩的也不一定。不過,不論如何,這只爐子已經可以肯定是宣德三年的,單憑這與衆不同的色澤和品質,就足以當得上當世名爐了。
當時張辰弄出那只小爐子的時候,寧琳琅并沒有在場,而張辰和褚鐵眼也并沒有認為是一件什麽了不起的事情,只不過是覺得比較有趣,當做是偶然得知的罷了,時候也并沒有跟別人說起過。現在遇到了實物,這樣的教學機會可是越來越少了,正好趁着這個機會,給寧琳琅說一下這裏邊的關鍵。